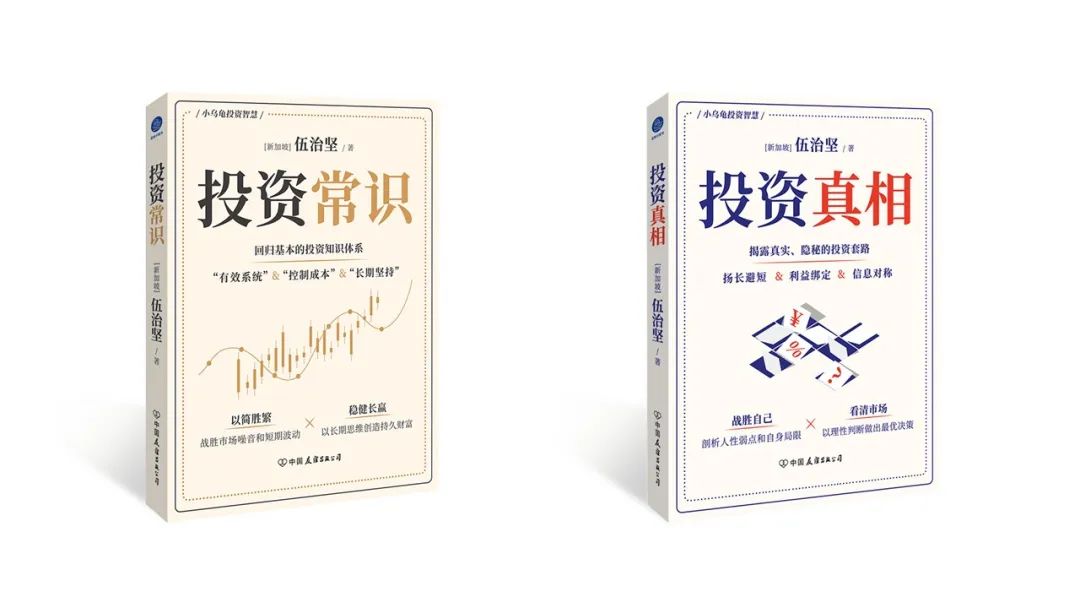长寿奖励为什么不受欢迎?
1693年的伦敦,街头空气里混着煤烟、马粪味,还有战争的焦灼气息。当时的英国正与法国打得不可开交,国王威廉三世为了筹措战争经费,可谓绞尽脑汁。为了应对日益恶化的财政赤字,英国议会一边加税,一边费尽心思想出各种奇奇怪怪的融资办法。
就在这样的背景下,一个新奇的金融发明登上舞台:唐蒂(tontine)。它的名字来自一个意大利银行家洛伦佐·唐蒂(Lorenzo Tonti),他发明了一种听起来像是“投资+游戏+寿命赌局”的产品。听上去有点复杂,但其实逻辑很简单:参与者每人出一笔钱组成资金池,政府承诺每年支付利息。起初大家都分红,但每当一个参与者去世,死者的那份收益会被重新分配给幸存者。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,活得越久,分得越多【1】。
听起来是不是很刺激?那简直就是17世纪的“金融版吃鸡游戏”。最后活下来的那位老人,理论上可以独享整个资金池的利息,简直比买彩票还刺激。设计者唐蒂的初衷,是希望用那个活的最长的幸存者的超高回报,来吸引足够多的人参与购买,这样为政府筹得所需的资金。为了筹资,当时的政府推出两种年金计划供消费者选择,第一种是固定年金,每年分发14%的分红。第二种就是tontine。
在当时的设计里,tontine 的名义利率是 7%。其规则是:每位参与者出资100英镑,政府按7%的年息率支付利息。当一位投资者去世,他的那份利息就会被重新分配给还活着的人,以此类推。活得越久,分得越多。
举个最直观的例子。假设你是1693年的伦敦市民,今年三十岁,刚在咖啡馆里听人介绍完 tontine 的玩法,决定也掏出一百英镑加入。政府承诺给整池资金每年支付7英镑利息,所有参与者平分。第一年,假设有一千名投资者,那么每个人都能拿到7英镑,简单明了。
第二年开始,情况就变得微妙了。假设一年里有十个人不幸离世,他们的那10份7英镑不会消失,而是被重新分配给剩下的990人。于是你在第二年拿到的利息就变成了7除以0.99约等于7.07英镑。也就是说,如果有1%的参与者去世,那么剩下的人能够拿到手的利息就上升1%。虽然只多了区区0.07英镑,但你能感受到这场“赌命游戏”的味道:死的其他人越多,你的收益就越高(假设你还活着)。
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推算:如果奖金池中的一半人去世,幸存者拿到的名义票息率就会翻倍,从7%上升到14%。如果只剩四分之一人,则升到 28%;若只剩十分之一,年息理论上会达到 70%。你越长寿,越到后面,回报就越像火箭一样往上飙。
问题在于,能活过别人的概率有多高呢?按照1693年的寿命表显示,一个30岁的人平均能再活30年,到60岁左右去世。但那只是“平均值”,并非一半人能活到60岁。事实上,到60岁时,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仍在世,而三分之二的人已不在人间。
这是寿命统计中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点。平均值并不是中位数,平均寿命也从来不等于“一半的人能活到这个年龄”。举个简单的例子。假设有三个人,30岁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。第一个人再活15年,到45岁离世。第二个人再活30年,到60岁离世。第三个人格外长寿,再活60年,直到90岁才离世。把他们的余命(15+30+60)加在一起再除以3,平均每个人都能再活35年,也就是说这个样本的平均死亡年龄为65岁。但事实上,三个人里只有一个,也就是三分之一,能真的活到65岁。另有三分之二的人,还没够到平均值前就已经去世了。
归根结底,背后的原因来自寿命分布的结构。极少数的极端长寿者,会把平均值大幅向右拖长,而大多数人并没有享受到这种长寿红利。读懂这一点,才能理解为什么 tontine 的游戏机制会让大多数参与者拿不到“纸面上的高收益”,也能理解为什么人类在面对风险时对平均值往往抱有错误直觉。
回到上面这个例子,当时一个活到平均寿命的普通投资者,大约能拿到10%—11%的平均年回报,而固定年金则是确定的14%。除非你能活得比同龄人多十年以上,否则你的总收益仍低于年金。这就是那场1693年大规模金融实验的残酷现实:tontine的上限令人兴奋,但平均值的吸引力并不强。
结果可想而知。90%的投资者都拒绝了 tontine,选择了固定年金。然而从结果看,tontine的实验失败,反而推动了英国财政的现代化。议会发现,原来人民更喜欢稳定的现金流,而不是赌博式的高回报。于是,政府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陆续发行各种固定利率国债,并通过国会立法保障支付。这直接促成了英国公共债务制度的建立,也让伦敦成为18世纪最可信的金融中心。
现在,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,把这场游戏规则稍微调整一下。假设政府把 tontine 的起始票息稍稍调高到9%。根据1693年的平均寿命精算表,参与tontine计划的人中,有一半人最终拿到的 IRR 会低于14%,一半人最终会高于14%,而处于中位数的那一批人,恰好拿到14%,和固定的年金收益一样。在这种情况下,人们会怎么选?
答案大概率仍然一样。人们仍会更愿意买固定年金。因为这时人们面临的选择,已经不是“收益高低”的比较,而是“确定性与不确定性”之间的抉择。
在两者收益相等的情况下,人类倾向于选择确定的那一份。这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·卡尼曼(Daniel Kahneman)所说的“确定性效应”(Certainty Effect):
当面对两个概率接近但不相同的结果时,人们往往会过度偏好那个“确定”的选项,即使它的期望值更低。
为什么人们偏好确定?背后有这么几个原因:
第一是损失厌恶。
在 tontine 里,如果你过早死去,你的本金“随你而去”,家人得不到任何回报。对人来说,这种损失的痛苦远大于潜在收益带来的快乐。简而言之,损失1块钱带来的痛苦,远远超过获得1块钱带来的满足。
第二是道德厌恶。
tontine的收益来自他人的死亡,听上去更像是一场集体赌命。对17世纪仍深信宗教伦理的英国人而言,这不只是风险问题,更是良心问题。
第三是控制幻觉。
固定年金让人觉得自己掌握未来,而tontine则让人感觉把命交给统计。即便从概率看,两者差距不大,人类也更愿意相信“我能掌控”的选项。
这三种心理力量,正是行为金融学的基石。它们并不代表非理性,而是一种“有限理性”,即带有边界的理性。回看tontine的故事,它给我们带来重要启示:数学能勾勒结构,却无法消除人心深处的不安。投资决策表面上是数字的较量,底层却是一场关于安全感的斗争。投资中,最难的从来不是算式,而是人心。
参考资料:【1】Thomas Levenson, Money for Nothing: The South Sea Bubble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, HarperCollins, 2020.
免责声明:上述内容仅代表发帖人个人观点,不构成本平台的任何投资建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