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 生物医药行业长期受到一个问题的困扰:创新周期往往比回报周期更长。
2. 在几乎所有治疗领域里,礼来的整体研发速度,平均仍然比下一家同规模的制药公司快大约40%。
3. CEO的工作职责是创造条件,让伟大的想法能够系统性地不断涌现。
4. 在过去10年里,我当初做过的一个最重要的决定,就是在公司还负担不起的时候,依然为英伟达建造了一台当时全球规模最大的超级计算机之一。
5. 我现在真的认为,生物医药行业的“关键时刻”已经到来了。能够从“药物发现”这种有点像在森林里找松露的方式,转向真正的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。
6. 当然,这背后的科学极其复杂,人类生物学本身也极其复杂,可能(完全实现)还需要10年时间。
7. 如果我们能把这件事从一种“手工艺式的发现”,变成一个工程问题,那对人类生命的影响将是巨大的。
8. 我们更关注一个更现实的问题:如果最大寿命上限是100岁,我们怎么让更多人更有机会真正走到那一天?而我们的方式,是通过消除疾病来实现这一点。
9. 如果说在AI领域目前最容易落地,也最可操作的方向,我认为是医疗服务。
在上个月举行的2026年摩根大通医疗健康大会上,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与礼来公司CEO戴文睿(Dave Ricks)在宣布重大合作后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,大约1小时。今天刚放出了完整视频。
两家公司将在旧金山湾区共建一个首创性的AI联合创新实验室,并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共同投入高达10亿美元,将AI技术彻底融入药物发现和生物医学研究流程。
两位掌舵者都无比兴奋。
对于生物医药行业来说,传统新药研发周期长、成本高、成功率低已成为公认的结构性难题。而AI具备高速模拟、海量空间探索和自动化协同的潜力,被视为可能改变这一格局的关键力量。
过去几年,礼来在代谢性疾病领域的突破已无需赘述。
以替尔泊肽(Tirzepatide)为代表的GLP-1药物,不仅在减重和糖尿病治疗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疗效,也正在显著改变慢性病管理的边界。
戴文睿在对话中反复强调的是一个更长期的目标:把药物发现从高度经验化的探索,推进为可以不断复制、持续优化的工程体系。
对话还提及,该合作框架未来将向生物医药初创公司开放,通过联邦学习等机制,在不共享原始数据、不损害知识产权的前提下,共同训练模型、放大创新效率。
看起来挺酷的。
值得一提的是,2026年2月4日礼来发布2025年财报,全年营收651.79亿美元,同比增长45%,预计2026年营收规模在800-830亿美元之间。财报披露当日礼来股价蹭蹭蹭涨了10.33%,一度重返万亿美元市值。
戴文睿在对话中反复提到的替尔泊肽合计销售额365.07亿美元,其中四季度销售额116.70亿美元。替尔泊肽全年销售额超过司美格鲁肽和Keytruda,正式登顶药王宝座。
聪明投资者(ID: Capital-nature)抱着学习心态整理精译主要内容分享给大家。嗯,考虑到篇幅,忍痛删除了一些两人逗捧哏的有趣过程。
延伸阅读:大赞中国新药研发实力!礼来CEO戴文睿最新对话,谈及制药业AI创新以及减肥药革命
加速药物研发速度以及如何更好接棒
黄仁勋 说起来,我们两个人的成长背景,几乎不可能更不同了。戴文是鹰级童子军,而我则上过一所“问题少年学校”。先澄清一下,我是被误送进去的,那并不是什么糟糕的学校,其实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,而且学费也很便宜。
所以回到正题。2017年,你成为了CEO。我的问题是:当时的礼来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?那时它对生命科学未来的愿景是什么?而今天的礼来又处在什么状态?在信念的层面上,你现在对生命科学未来的看法又是什么?
戴文睿 2017年的时候,礼来刚刚超过140年,是一家相当成熟、根基深厚的公司。不过,在那之前,我们的行业经历过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,这一点稍后我也可以再展开讲。
正如在座很多人所知道的,我们这个行业长期受到一个问题的困扰:创新周期往往比回报周期更长。
平均来看,你会不断经历高峰和低谷的循环。
而在低谷期,你要么撑不过去,被并入其他公司,最终只剩下别人公司名字后面的一个“连字符”;要么就学会如何活下来,并做出极其艰难的决策。
我认为,礼来几乎是唯一一家在经历这些周期时,没有通过并购或合并来渡过难关的大型制药公司。
我们已经经历过好几轮这样的周期,因此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在艰难时期具有生存韧劲的组织DNA。
其中有一件事对我触动非常深。当时我已经是执行委员会的一员,我们经历了2010、2011、2012 年那一轮周期。那段经历让我意识到,在发明和创新这件事情上,你必须极端地、持续地保持强度。
因为这个时间周期非常残酷:一旦你遇到专利悬崖,却又没有任何产品可以接续,你就不得不对整个公司进行重塑。
想象一下,每隔10到15年就来一次这样的过程,组织根本不可能积累真正的动能。人会离开,隐性知识会流失等等。
于是我们开始着手应对这个问题。我认为大致有两种路径。
第一种是说“那我们就要有更好的点子” 。但正如你们所知道的,这很难长期维持。即便你一度有很好的想法,外界也觉得你很聪明,现在大家对礼来的看法就是如此,但这种状态是很难持续的。
所以我们当然也在努力提高发明本身,但更重要的一件事,是加快发明的速度。
我们系统性地拆解了整个研发流程,几乎是逐个环节来做,从候选分子的选择到第一次获批,中间有上百个步骤,我们把时间一段一段地压缩下来。
直到今天,在几乎所有治疗领域里,礼来的整体研发速度,平均仍然比下一家同规模的制药公司快大约40%。
这意味着,我们可以在专利周期之内完成真正的发明,然后公司才有可能重新进入增长轨道。
这在2017年还只是一个设想,而现在已经被真正落实了。
与此同时,我们也做了很多事情来推动更多的发明。我们很幸运,在2006年就较早押注了一个叫GLP-1的方向,并推出了全球第一款相关产品。
当时几乎没人听说过这个概念。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反复摸索、不断尝试,大概折腾了12年。对整个人类来说,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。
黄仁勋 听起来像个芯片名字,GLP-1。
戴文睿 确实有点像。你是不是想问,会不会有GLP-2、GLP-3?
确实有GLP-2,那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蛋白,不过作用基本相反。我们并不希望把这两种激素结合在一起,因为市场非常小,我得说,真的非常小。
我并不是医疗专家,但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,现在我们其实已经算是在“GLP-2”阶段了,因为替尔泊肽(Tirzepatide)是把两种蛋白融合在一起的,而这是我们开发出来的一项技术。
接下来还有一个三重作用机制的分子,预计在2027年推出,那会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阶段。
不过总的来说,我们抓住了这一波浪潮。最初是竞争对手在肥胖领域率先完成了创新,而我们随后追赶并执行得相当不错,最终在去年成为了市场领导者。
所以现在,我们不仅拥有一台更快的创新引擎,而且还处在一个由单一理念带来的巨大成功周期之中。
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是:如何在这一轮成功周期结束之前,就提前找到下一轮成功,并获得持续向前的速度。
这件事,坦率说,行业里还没有哪家大型公司真正做到过。大家一直只是经历一轮又一轮的周期,而我们的目标,是打破这一点。
(聪投注:这段让人想起3万亿美元的近百年的资管巨头资本集团(Capital Group)。其历史上最杰出的分析师之一——杰森·皮拉拉斯(Jason Pilalas)在职业生涯中,正是通过对单一突破性产品的前瞻判断,捕捉到一批伟大的医药投资机会:因胃溃疡药物泰胃美(Tagamet)押中史克,因善胃得(Zantac)投中葛兰素,又因降压新药依那普利(Vasotec)看准默克的长期潜力。这些成功案例为资本集团带来过丰厚的回报。
但同样重要的是,当他意识到某些公司在核心产品之后缺乏清晰、可验证的后续研发接力时,即便当期业绩仍处高峰,也会选择退出。资本集团内部始终坚持一个判断:医药公司的长期价值,不取决于“这一款药有多成功”,而取决于“成功是否能够被接续”。这恰恰呼应了戴文睿在对话中的核心命题——真正困难的,不是创造一次突破,而是在每一次产品周期之后,为下一次增长提前铺路。)
CEO的根本职责是创造条件
黄仁勋 你刚才提到的一点,其实我经常对我的员工说,CEO的根本职责,并不是亲自去想点子。我们的工作是创造条件,让伟大的想法能够系统性地不断涌现。
你刚才描述的,本质上就是礼来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智慧:必须创造出让这些重大创新得以发生的条件。
我们以前也聊过英伟达早期进入AI领域的事情。回头看,英伟达做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,就是在基础设施上提前下注,去创造条件,让最优秀的AI研究人员愿意加入我们,从而让伟大的发明自然发生。
今天我们对这件事其实讲得不多,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,在过去10年里,我当初做过的一个最重要的决定,就是在公司还负担不起的时候,依然为英伟达建造了一台当时全球规模最大的超级计算机之一。
那时,甚至没有多少AI研究人员能真正用得上它。
如果你想吸引世界上最顶尖的粒子物理学家,却没有大型强子对撞机,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这也把我们的对话自然引向了一个结论:AI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进展,使我们有可能把它应用到人类最非凡、也最困难的挑战之一——生物学。
于是,我们两个人就开始设想,如果全球最大的计算与计算机科学公司,能够与全球最重要的生命科学公司展开深度合作,会发生什么?
这就好像我们共同创建了一间实验室,在某种意义上把两家公司当成一家公司,把所有最顶尖、最不可思议的能力整合在一起。
戴文睿 非常令人兴奋。今天我们正式宣布了这项合作。这项合作大致分为四个部分。
首先,我们采购了大量芯片,并正在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、专门用于生物学研究的本地部署超级计算机,预计就在本周完成。这台计算机将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,这里本身就是全球生物药物发现的重要中心。
在超级计算这件事之外,我们还会在湾区组建一支研究团队。如果有优秀的科学家或者计算机科学家想加入,这将会是一个礼来—英伟达联合的 AI 实验室。
我们还会着力开发全新的数据。因为任何真正了解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,你可以训练模型,但如果数据“只有一英寸厚”,你是走不了多远的。
而生物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未知的。所以,我们需要为了训练机器而开展大规模的实验,持续生成数据。
接着,我们还要在英伟达已经构建的模型基础之上继续往上“爬梯子”,做出更复杂、更高级的预测。
从“手工艺式的发现”变成一个工程问题
黄仁勋 理解AI的一个重要方式,是把它想象成一块多层蛋糕。
最底层,你需要能源来驱动这些计算机;再往上一层,是计算机里的芯片;再往上,是基础设施层。这一层本质上是在解决这样的问题:如何让计算机学习?如何处理数据?如何设置安全护栏?如何微调?如何教学?
这层有点像AI的人力资源部门,只不过他们的工作效率要高得多。
在基础设施之上,是模型层;再往上,是领域特定的数据和飞轮机制。
真正令人兴奋的一点在于:我们可以训练模型来合成蛋白质或化学分子,把这些结果送进机器人实验室进行实验,收集新的数据,再把这些数据反馈回模型中。
这个飞轮——用AI生成蛋白或分子、进行真实实验、获得现实世界的数据,再把整个科学飞轮加速运转。这样的未来,令人无比兴奋。
所以,我们正在系统性地把药物发现领域中最优秀的专家,与计算机科学领域中最优秀的人才聚集到一起。
在我们的联合创新实验室里,基本上会覆盖这块“蛋糕”的每一层,希望最终能勾勒出一幅关于未来药物发现的蓝图。
大概在40多年前,准确地说是43年前,我属于第一代工程师,那一代人第一次迎来了“计算机辅助设计”这个概念。
在我之前的工程师世代里,他们会设计一款芯片,可能会成为一次成功,但接下来好几年都没有新的突破;再设计一款,又成功一次,然后又停滞几年。
戴文睿 现在这个行业已经完全不是那样了。
黄仁勋 没错。而我们这一代人出现之后,第一次能够用软件来表示晶体管、逻辑门和系统功能。
计算机终于可以准确地表示你的领域,并模拟它的行为,尽可能在硅片里完成设计和验证。
今天我们设计的是极其庞大的系统。大约有1.5万人共同参与一套计算系统的设计。我们刚刚完成了Vera Rubin的流片,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研发费用。
最终完成的计算机重达三吨,包含大约150万个部件、6颗全新芯片,总计220万亿个晶体管。
而最关键的是,它第一次运行,就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。每一代系统,都是在上一代基础上构建的。
我现在真的认为,生物医药行业的“关键时刻”已经到来了。
经过百万倍、甚至更高数量级的算力提升之后,我们终于也许能够表示并理解世界上最困难的问题之一——人类生物学。
能够从“药物发现”这种有点像在森林里找松露的方式,转向真正的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。
顺便说一句,礼来当年真的有一个“土壤发现部门”,会派人去热带雨林采集土壤样本,带回印第安纳波利斯,从中提炼出后来变成抗生素的物质。
事实上,医院里最重要、也是最后防线的抗生素之一——万古霉素,就是礼来在婆罗洲的一份土壤样本中发现的。
那他们当初怎么知道要去哪里?其实也不知道,只是因为真菌会产生对抗细菌的天然机制,于是他们就去挖土、去找这些天然防御体系,再把它们转化成药物。
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药物发现”。
你仔细想想,这种工作方式是有生命风险的,甚至可能得疟疾。那是1950年代的事情,距今已经70年了。
但现在不同了。现在,你们的工作方式开始变得像我的工作一样,基本不用离开办公室。
戴文睿 是的,全都在屏幕里完成。
黄仁勋 所以,真正让我感到兴奋的是,我们也许真的能够实现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。当然,这背后的科学极其复杂,人类生物学本身也极其复杂,可能还需要10年时间。
但我真心认为,这次我们之间的合作宣布,可能会成为某种起点,一种蓝图的开始。
戴文睿 我也希望如此。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突破。
你在摩根大通的大会上会看到,行业里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研发管线,但其中大多数成果,都是一点点凿出来的,是非常艰苦、非常经验主义的过程。
偶尔我们能借助一些系统性突破,比如单克隆抗体,本质上是“劫持”了生物体自身解决问题的方式。
但大多数时候,每一个小分子发现都像一件艺术品,独一无二,稍有偏差就前功尽弃。
如果我们能把这件事从一种“手工艺式的发现”,变成一个工程问题,那对人类生命的影响将是巨大的。
关于GLP-1的机理以及更多价值
黄仁勋 回到GLP-1。你刚才提到,它其实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了。那么接下来会走向哪里?还能用来做什么?
戴文睿 事实上,肥胖是成年人慢性疾病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枢纽变量。
很多当下的疾病,在人类进化史上根本不是问题。我们进化得太慢,而环境变化得太快,于是出现了错配。肥胖正是这种错配的产物。
我们是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环境中进化出来的。在人类进化过程中,其实并不需要为“饥饿”设计一个关闭开关。因为当时的世界并不存在“过剩”这个概念。
现在不一样了,现在的关键词是“丰裕”,是过剩。不论是热量、智能,还是生产力,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高度丰裕的世界里。至少对我来说,我的生活几乎被各种各样的“过剩”所包围。
但问题在于,我们现在也处在一个热量极度过剩的环境中,而进化并没有提前为我们设计好一个“停止进食”的机制。
从进化角度看,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。所以我们才会出现肥胖问题,而肥胖又会引发大量慢性疾病,折磨人类,甚至缩短寿命。
如果我们能拥有一套相当有效、而且还会不断变得更有效的工具去真正帮助人们管理体重,用一种人工合成的方式,帮身体装上一个关闭开关,那么我们就有机会下调、甚至显著缓解200多种慢性疾病。
黄仁勋 真的有这么多?
戴文睿 确实如此。接下来24个月里,会发生两件非常重要的演进。
第一,是选择会显著增多。GLP-1本身只是一种肽,但它属于一个家族。
通过在替尔泊肽中把GIP和GLP结合在一起,我们已经看到药效更好、耐受性也更强的结果。未来你可以预期会看到更多类似的组合。
在这个“超级蛋白家族”中,我们可以整合不同成员的优势,做出更容易耐受、同时效果更强的药物。
不论是在维持阶段、诱导减重阶段,还是针对不同患者特征的个性化需求,都会有更多方案出现。正如我刚才提到的,我们的三重作用分子也在推进中。
而单纯的体重下降,本身就会带来极其广泛的下游好处。这也引出了第二个重要变化:应用场景的拓展。
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,使用Zepbound(替尔泊肽减重注射液)后,平均体重可下降约23%。但真正逐步显现的,并不只是减重本身,而是一系列原本可以预期、却远比想象中深远的连锁结果,包括心梗风险下降,整体代谢系统明显改善。
在糖尿病与糖尿病前期人群中,向糖尿病发展的转化概率下降了93%。可以设想,如果在全国范围内,为约7000万名糖尿病前期人群提供 Zepbound,美国的糖尿病患者规模在理论上将大幅收缩。
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发现。若与特朗普政府刚刚签署的医保准入协议能够顺利推进,或许真的有机会向这一方向迈出实质性一步。
除此之外,还有一些不那么直观、却同样关键的作用机制,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炎症。肥胖所引发的,并非一次性的急性反应,而是一种长期存在、系统性的慢性炎症。这种状态持续侵蚀心血管系统,加重关节负担,也会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损害身体机能。
在早期临床试验阶段,我们就开始自发地听到患者的反馈:他们不仅体重下降了,而且有人说,这是十年来第一次能够轻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;膝盖不再像以前那样疼;背部的不适明显缓解。还有一些患有克罗恩病或结肠炎的患者,甚至报告症状几乎消失。
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?关键在于,我们并不是在处理某一个孤立症状,而是在系统层面降低了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水平。基于这一机制,我们已经启动了一系列针对不同疾病的研究。
上个月公布的首项结果显示,在银屑病关节炎患者中,在原有基础用药之上联合使用Zepbound,整体疗效提升了约50%。
接下来,这些潜在应用将以医学体系能够接受的方式逐步推进——也就是通过清晰、可验证的适应症,让创新真正进入临床实践。
黄仁勋 这和AI的采用路径其实很像,你也需要在具体场景中证明它的价值。
戴文睿 完全一致。我们已经启动了一系列脑健康相关研究,并且专门为神经系统疾病设计了GLP-1 / GIP的特定组合,其中一个重点方向就是成瘾问题。
成瘾,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代社会挑战。有意思的是,这类药物抑制食欲的机制,其实并不只是因为身体需要更少的热量,而是因为它们作用于一些后天学习形成的行为回路。
听起来是不是越来越像AI了?同样的机制,也可能适用于其他具有自我强化特征的有害行为,比如赌博、饮酒,甚至戒烟。
因此我们也在系统性地探索这些方向。当然,我们希望它不会影响那种工作过于拼命的行为。
黄仁勋 对,那可不行。
戴文睿 放心,只会针对不良行为。事实上,这些行为在模式上,与过度进食高度相似。
顺便说一句,这是给在座各位创业公司CEO的一个友情提醒: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意志力开始下降了,先停一停微剂量试验。
黄仁勋 现场可是有不少创业CEO。
戴文睿 目前大家也在同步研发作用时间更长的方案,以进一步降低用药频率。今年春天,我们还将推出口服GLP-1。这不仅是使用便利性的突破,更重要的是一次全球可及性的突破。
从外表看,我们现在的自动注射装置似乎很简单,但从制造角度来看,这其实是全球最复杂的药物之一,而且面临的是数亿人次级别的需求规模。
我们刚刚在中国、印度以及东南亚推出产品,而这些地区的肥胖问题同样非常严峻。仅依靠注射制剂,根本无法满足需求,尤其是在东南亚,那里糖尿病负担极其沉重。
某种意义上,东南亚人群在肥胖问题上“输掉了遗传彩票”:在更低的体重水平下,哪怕是小幅度的体重增加,也更容易触发一系列疾病。因此,我们必须具备大规模生产能力。
口服制剂在化学层面实现,不依赖蛋白合成,也不需要无菌注射系统——只是一颗药片,就能实现极大规模的扩产。这一产品也将于今年上市。
黄仁勋 也就是说,这一个想法,你们还可以再跑五十年?
戴文睿 我们是这么希望的,也是在向你学习。
GLP-1的发现过程以及之后的重点
黄仁勋 当然,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是:能否持续不断地发明出足够好的新产品,让人们愿意为其付费,从而跨越专利周期?历史上有没有哪一种生命科学技术,曾经如此广泛地造福人类?
我能想到的,可能只有抗生素这一整个药物类别。
戴文睿 没错。
黄仁勋 青霉素的发现,几乎创造了现代医学。如果没有抗生素,就不可能有现代牙科、现代外科。今天我们已经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。
但从弗莱明在实验室里发现那团奇怪的霉菌开始,这开启了一条持续60年、诞生100多种新药的创新浪潮。
我觉得,GLP-1也可能属于这样的技术浪潮。不同之处在于,它针对的不是急性感染,而是现代智人所面临的慢性疾病。
戴文,你有没有意识到,你的工作听起来竟然会这么“轻松”?我太太也问过我这个问题。
为什么我不来你们这儿工作?一次伟大的发现,然后几十年都在享受红利。你们在森林里挖着挖着,就挖到了GLP-1这颗“松露”。
戴文睿 其实历史并不是那样的。
这个故事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。当时,一位德国科学家发现了所谓的“促胰岛素效应”(incretin effect)。GLP-1正是这一激素家族中的一员。
这类激素由肠道分泌,用来向全身传递一个信号:你已经进食了。
他观察到,如果将糖分通过口服方式给予人体,与静脉注射相比,胰岛素的反应完全不同。胰岛素本身是一种促进糖吸收的激素,而在口服条件下,这一反应明显更慢。这一现象提示,肠道的参与会改变整个系统的反应路径。
到了80年代,研究人员首先发现了GIP,随后发现了GLP-1,这正是Zepbound的两个组成部分。
此后,人们又陆续识别出更多相关激素。但始终存在一个核心难题:这些靶点极难做成真正可用的药物。天然GLP-1在人体内的半衰期只有大约7分钟。
如果直接使用这种天然肽作为药物,患者就需要全天候持续输注,这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行。
直到我们逐步学会将作用时间从每天两次延长到每周一次,如今甚至在探索按月给药的可能性,GLP-1才真正具备了成为产品的基础。
而在AI药物发现领域,已经开始显现效果的一点是:我们可以生成海量的组合方案,在计算环境中进行筛选,再从中过滤出真正具有潜力的候选物。
我们已经在规模化地推进这项工作,而通过这次合作,规模还可以再放大一个数量级。
黄仁勋 那我们能不能用AI找到更多生物学靶点?那才是真正的“圣杯”。因为如果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,我们就有可能一次性对整个系统进行建模,那会非常、非常令人兴奋。
还有一件事,是戴文一直特别想做的——把这个AI实验室、这个联合创新实验室放在这里。放在硅谷,甚至就在这座“AI之城”的附近。
旧金山确实是很多AI研究者的聚集地,我们在这里也有办公室。所以,这个实验室要么设在南旧金山——那一带是湾区的生物科技中心,要么就设在这里。
戴文睿 没错。我们想去人们真正愿意生活的地方。
黄仁勋 说到GLP-1以及它之后的东西,硅谷现在有不少人在聊长寿、聊延缓衰老。那你跟我讲讲,这背后的技术路径是什么?
戴文睿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。它当然对很多人都有吸引力,毕竟谁想变老呢?
细胞为什么会“到期”,这里面有很多生物学机制,你可以把它外推到细胞系统,再外推到器官,最终甚至外推到整个个体。但正如我们在台下聊到的,那不是我们现在主要的工作方向。
那条路径的核心问题,是能否把人类在理想条件下的最大寿命上限进一步往后推。
比如说,在理想条件下人可能活到100岁,然后系统出于某些原因就关闭了。坦率说,如果人能永生,那世界会很奇怪。那我们为什么要繁衍?我们怎么进化?这里面有很多问题,甚至是哲学层面的:自然的“原始设计”要怎么自洽?
我们更关注一个更现实的问题:如果最大寿命上限是100岁,我们怎么让更多人更有机会真正走到那一天?而我们的方式,是通过消除疾病来实现这一点。
你如果回看1900年的美国,男性的预期寿命大约只有46岁。最主要的原因,并不是人老得快,而是儿童死亡率极高。大量人群在很小的时候,就因为感染等原因去世。
随着抗生素、疫苗,以及一整套控制儿童疾病的医学工具出现,预期寿命迅速被拉升。
从1960年到今天,我们又大约增加了10年的预期寿命,这一阶段的提升,主要来自慢性病管理能力的持续进步。
癌症治疗取得了巨大突破,在座的很多公司,都在慢性病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;HIV/AIDS 以及其他新型病原体,也被逐步控制。
今天,美国的预期寿命已经接近80岁。事实上,如果不是阿片类药物滥用和交通事故死亡率异常偏高,这个数字可能更接近84岁。
而这两项,在美国都显著高于其他发达国家。自动驾驶或许能解决其中一个问题;另一个问题,也许GLP-1能发挥作用,因为我们已经开始研究它在阿片成瘾上的潜在影响。
我们正是通过这样一项一项、系统性地推进,不断拉长人类的健康寿命。当然,随着人活得更久,与衰老相关的新问题也会随之出现。
对我来说,在GLP-1之后,我最兴奋、也最关注的下一个前沿,是痴呆症以及与衰老相关的脑部疾病。
当我们的身体可以支撑我们走到八十岁、九十岁,大脑这件事,却还远没有被真正解决——无论是对生活质量,还是对寿命长度来说,这都会变得至关重要。
我们已经在这一领域投入了大量精力,也有一些令人期待的项目正在推进。从药物发现的角度看,如果我们能够模拟脑组织,去寻找新的靶点,并理解那些我们目前尚不清楚的靶点之间的相互作用,也许就能打开新的突破口。
衰老的大脑中,同时存在炎症和蛋白质错误折叠等问题,那里可能正隐藏着下一代治疗的关键。
关于联合创新实验室的构想
黄仁勋 如果我们退一步来看这间联合创新实验室,第一件事,其实是把计算平台搭建好,让研究者能够真正开展工作。
所以我们有算力、有基础设施层、有BioNeMo,也有一整套已经构建完成的模型和模型架构。接下来,就是把科学家聚到一起,在这些基础之上开始协作。
但如果你要给研究团队一个愿望清单,你最希望他们把精力放在哪个方向?
戴文睿 我觉得可以先把问题简化为两个方向。当然在每个方向里,我们都需要进一步聚焦,只有这样才能持续推进,也才能形成可交付的成果。
第一个问题,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已经有相当的动能了,也就是工程化的药物设计。
今天很多药物,本质上都属于这一类:靶点已经存在、也被充分研究过,真正的挑战在于,如何更精准地定制那把“钥匙”,去匹配那把“锁”。
与此同时,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治疗范式,比如RNA、基因疗法等。这些技术出现的时间还不够长,还远没有被充分优化。
所以我认为,围绕药物工程和药物优化这一整套问题,本身是相对可解的,而英伟达的科学家与我们的研究团队结合起来,很可能在这一领域较快取得实质性进展。
这类成果,也非常适合通过Tune Lab这样的接口开放出来,与更多生物科技合作伙伴共同使用。我们可以把“更好的药物制造”这件事,通过计算机内的设计与工程化,真正推向规模化。
简单解释一下Tune Lab:这是一个平台,让礼来能够与初创公司或第三方一起合作,共同推动某个具体方向的进展。
它基于联邦学习的技术框架,底层是我们贡献的NVFlare。研究者不需要集中或混合数据,却仍然可以共同训练模型,从而实现协作式创新。
自从我们宣布合作以来,几乎一整天都有初创公司主动来询问如何参与Tune Lab 和联合创新。
Tune Lab的构想非常有前瞻性,它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、却极其棘手的问题:如何在保护数据与知识产权的前提下,让不同公司的AI研究者真正协作。
我们不收取费用,但会进行筛选,确保项目是严肃、可信的生物科技研究。合作的成果,也会被整合回Tune Lab,让不仅是礼来的科学家,更多生物科技研究者都能从中受益。
第二个问题,是靶点本身。在这一点上,我认为机器人实验体系必须真正发挥作用。
为什么我们可用的靶点还不够多?为什么我们对已有靶点的理解仍然不够深入?很大程度上,是因为它们的结构和行为,比我们以为的要复杂得多。
药物研发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,正是我们以为理解了靶点,但实际上并没有。
这背后需要的是围绕关键靶点,获取海量、系统性的实验数据,把它真正“刻画清楚”。
我们已经有机器人湿实验室在运行,但接下来会建更多,让它们24小时不间断工作,在一个靶点空间内持续实验、持续生成数据,形成完整画像,再与工程化药物设计结合。
这条路更难,也更偏经验主义,但机器天生适合日夜不停地做这件事。一旦这个飞轮转起来,它会转得非常快。
AI领域目前最可操作的可能是医疗服务
黄仁勋 戴文,如果你回头看我们在其他领域取得的一些突破,第一件事往往是:你最终必须让这个飞轮落到现实世界。
你得做真实的实验,收集真实的数据,用它把闭环跑起来。随着循环推进,模型会变得足够好,基础模型会变得足够强,你就可以教它去生成、去做生成式工作。
最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形态:一个模型在不断与另一个模型对抗、验证。而那个“另一个模型”,其实就是“世界模型”或者“靶点模型”。
靶点模型会和你训练中的模型一起,在一个闭环里运行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实验室本身也在变成一个模型。
当然,你最终还是要重新落地,真正去合成蛋白,产生真实数据。
但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会进入一个合成数据飞轮:先在模型里生成、再在模型里筛选、再用真实实验去校准。
这个飞轮的效率极高。我认为在我们这个行业里,以往从未有人以这样的规模去尝试,而我相信我们会在这里做到。
真正关键的是,挑选出少量我们高度怀疑与重大疾病密切相关的靶点,然后在机器人湿实验室里对它们做完整、系统的刻画,用实验数据训练数据集,再让机器去填补中间的空白、扩展整个空间,最终做出更好的药物——因为我们真的理解了这些靶点。
这实在太令人兴奋了。我认为这可能是第一次,我们拥有一个在专业深度和规模上都足以吸引顶尖人才的实验室,让他们愿意把一生投入到这个交叉领域。
这场大会有一件特别棒的地方,就是大型公司和小型公司能够聚在一起。你这边看到了哪些公司?哪些方向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?
戴文睿 我看到的方向很多。比如机器人实验室相关的公司、AI 科学家团队,当然也包括代理式医疗(agentic healthcare)相关的公司。像Abridge在做的事情,还有Open Evidence,也都非常、非常酷。
如果说在AI领域目前最容易落地、也最可操作的方向,我认为是医疗服务。
这当然不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问题那么复杂,而是如何用代理式AI服务去替代或增强人类层级的服务。这是整个经济体系里生产率最低的部分之一,从逻辑上说,采用AI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选择。
但现实里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。我们经常讨论怎么合作、怎么推动。
比如我们现在运营着全国规模最大的直达型药房平台之一,是真正意义上的直销。业务才一年,但目前年化已经接近每季度10亿美元,也就是一年约40亿美元的药房销售规模。
于是很多团队会问:礼来能不能用你们的市场体量去推动这些新技术的采用?坦率讲,保险公司并不喜欢改变,医生群体对这些技术也会有顾虑。
但我们确实需要让美国医疗系统变得更高效。只有这样,才能为创新、为前沿药物的采用腾出空间,也才能对患者做更准确、更全面的评估。
与此同时,正如我之前提到的,过去十年里,即便没有把AI完整引入主流程,药物研发在一些新范式上的生产率其实也在加速。这令人兴奋,但仍处在早期阶段。
现在很多公司在把新旧范式组合起来,做成“双功能药物”:一端是靶向部分,另一端是“战斗部”,比如用于杀伤癌细胞。甚至只是更精准地把药物送到正确组织,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、也非常难的工程问题。
今天我也见了几家在做不同路径探索的公司,对我来说都很有意思。这是药物制造这一侧。
我认为AI能在这里继续加速进展,而且已经有很多聪明的人在解决这些问题。
戴文睿 说真的,十年前、也就是你刚才问到的2017年,礼来的外界形象,可能还是一家有点“昏昏欲睡”的中西部公司。但给在座的计算机行业朋友们讲几个有意思的事实。
你可能不知道,第一个获批、由活体生物制造出来的生物技术药物——用最现代方式生产的药物,其实是礼来的产品Humulin,是我们和 Genentech 合作完成的。
黄仁勋 哦,那挺酷的。
戴文睿 然后在12年之后,礼来买下了制药行业里的第一台超级计算机,把它放在了印第安纳波利斯。那是一台Cray超算名字叫 Big Red,顺便一提,我们公司的标志也是红色的。
黄仁勋 Big Red。
戴文睿 对,很巧妙。后来我们正是在那台机器上,设计出了第一款由计算机设计并最终获批的药物——胰岛素赖脯胰岛素(Humalog)。直到今天,它仍然被全球大量一型和二型糖尿病患者使用。
当时我们基本上就是通过不断尝试不同的氨基酸序列,用相对经验的方法把这件事做成的。
黄仁勋 你一直在试图说服我,说礼来其实很酷。
戴文睿 我们确实很酷。
—— / Cong Ming Tou Zi Zhe / ——
排版:关鹤九
责编:艾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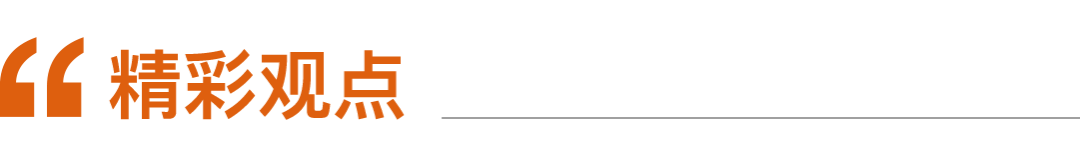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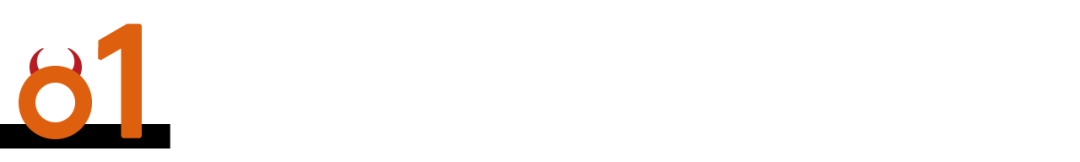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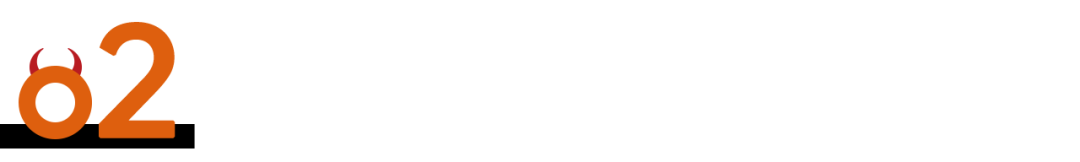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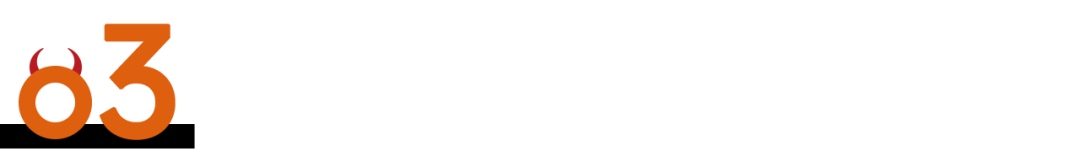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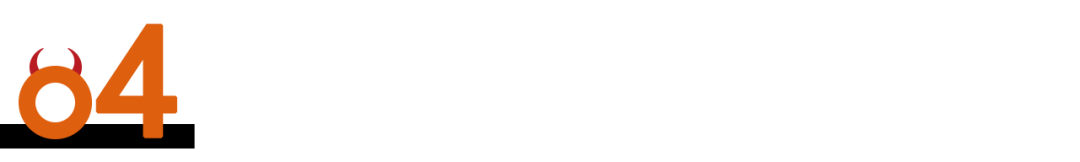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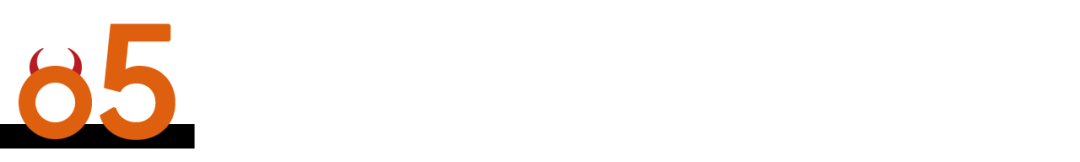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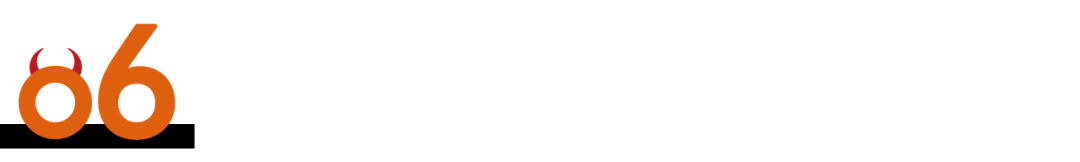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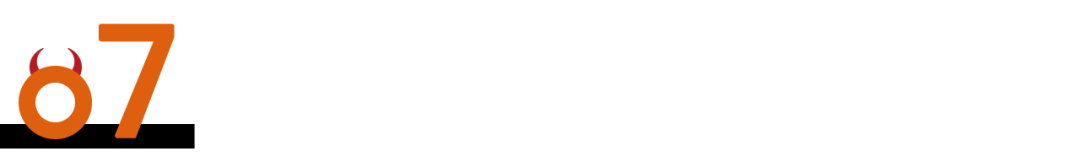
精彩评论